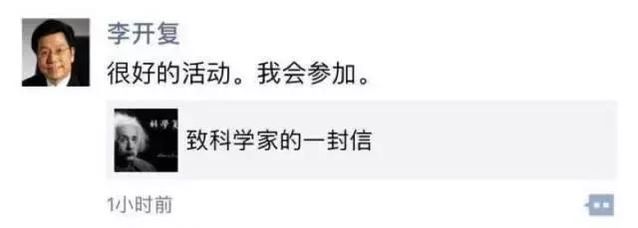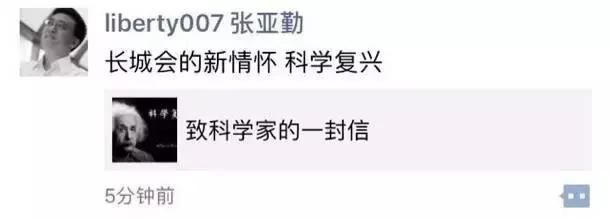文 | 阑夕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有一首歌叫做「感觉身体被掏空」,里面是这样描写绝大多数上班族所面对的会议的:
有一个老板叫做 大卫
下午六点出现眼神恰似黑背
手里端着一壶热腾腾的 咖啡
嘿嘿嘿
我们要不要来开个会
当「开会」成为令人生畏的折磨手段之后,我们已经遗忘了人类这种群居生物曾经在会议上营造出的群星璀璨。
自300万年前的人类开始集体狩猎时,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就已经被写入了历史的骨髓之中。也许正是于此同时,人类学会了用会议去解决那些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如何面对明天的猛兽,如何订立血缘家族公社内的秩序。此后人类智慧的发展和传递,不再孤立于个体之中。
就像亚里士多德说过的,「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
雅典文明一直是历史中最奇特的一束光耀,尽管理智上来说所有人都知道它拥有着悲剧性的缺陷,却丝毫不妨碍它被崇拜和向往。除开那些启蒙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学术对话,雅典的每一次公民会议都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未来。
五百人会议从公元前六世纪持续到公元前三世纪,近3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克里斯提尼完成了对雅典的改革后,十个按照地区划分的部落取代了过去的四个氏族部落,来自这十个部落的500位议员每日聚集在一起商议决策、审核提案、接待外宾。尽管时至今日有人诟病这500位代表来自有限的阶层,但是五百人会议上所坚守的原则和理性却的确被沿用至今,民主、自由、平等,简单却分量十足的六个字穿越千年的时光,响彻在亚哥拉市集的大会堂里。
现代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以后,似乎逐渐走向一条孤单的道路。实验室,仪器,埋头演算的公式,坚定而漫长的测量。但是无论有多少鸡汤煲着「在科学路上孤身前行」的曲调,人类的文明和智慧依旧是以集体的力量在前进。而会议这种最简单原始的集结众人智慧的方式,往往会成为科学之路上知名的地标。
第五次「索尔维会议」 | 量子交锋
1911年,比利时的工业化学家欧内斯特·索尔维在布鲁塞尔邀请到了包括居里夫人在内的科学家们举行了第一次索尔维会议。此后,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中断,但是每3年一次的索尔维会议依旧用自己的18次召开,记录下了世界物理学70年来的脚步。
与其它的传统学术性会议不同,索尔维会议的聚焦点并不在学术成果的发表,而侧重于讨论物理学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很显然从这个定位就能看出,它注定火花四射,毕竟每位科学家血管里都还流淌着雅典辩论的热血。
于是在1927年10月,第五次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坦和玻尔这对已经唇枪舌剑了7年的好友,硬生生将原本讨论磁力的会场拉进了量子力学中,然后开始了物理学上最著名的一次旷世交锋。「玻尔,上帝不掷骰子。」「爱因斯坦,别指挥上帝怎么做。」这两句极富戏剧性的台词,将哥本哈根学派和爱因斯坦之间的争斗升华到了街知巷闻的级别。
后来玻尔和哥本哈根学派成就了量子力学,而爱因斯坦耗费一生试图去证明量子论的谬误。直到他们去世之后,关于量子力学的争论也依旧持续。虽然时至今日量子力学已经成为了物理学界的基石之一,而诸多实验也逐渐证明爱因斯坦的错误,但是当年那场趣味十足的交锋的确是量子力学的标志起源之一。
实际上,第五次索尔维会议即便没有这场著名的量子交锋,也早就被铭记史册。因为当时与会的29位物理学家中,先后有17位获得过诺贝尔奖。而这张著名的与会人员照片,已经被全世界的社交媒体传阅无数次,被网友们戏称为物理界的豪华套餐。
「基础物理的未来」讨论会 | 集体改行
这是一次在柏林召开的非常普通的学界会议,时间坐标是1933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次物理学界的会议,竟然载入了生物学界的史册。
其实事件经过了前前后后多年的发酵,首先是19世纪末伦琴发现了X射线以及其应用方法,随后就是发射性同位素的发现让人们对原子结构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除此之外,还有一连串分子生物学的基本技术条件被物理学和化学搭建完成。接下来,又轮到了玻尔出场。
1932年,玻尔在哥本哈根一场关于辐射治疗的会议上——没错,又是开会的时候——发表了一份名为「论光和生命」的演讲。这份演讲表达出他当时正在沉迷的哲思,有些艰涩难懂,然而他的学生德尔布吕克却敏锐地抓住了其中的端倪——测不准原理也许可以扩展到物理学以外的地方,例如用来将目前未解之谜最多的生物学推动到比原子层级更深远的程度去。
于是接下来的一年,1933年的「基础物理的未来」上,当时正在研究铀原子分裂的德尔布吕克宣布,自己将会转投生物学的怀抱。甚至于在这场物理学的研讨会上,大家一致得出了三个有趣的结论:一,物理学未来一段时间不会再有新的有趣理论了;二,生物学值得解决的问题最多;三,一批物理学家都会转投生物学领域。
不久后,那位拥有一只猫的薛定谔甚至还写了一本书「生命是什么」来推波助澜,不仅为德尔布吕克站队,还结合他的理论提出了更多引人入胜的理论方向。于是一时之间,一大批物理学家真的先后加入了创立分子生物学的行列之中。转行后的德尔布吕克开始投身噬菌体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最终引导和推进了上世纪最著名的生物成就——DNA。而他本人也在1969年的时候和其它两位生物学家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
1968年软件工程大会 | 剿灭危机
第一台计算机的故事已经被人讲过太多次,感谢战争一次次将人类的科技水平逼到了爆发的顶点上。而实际上每一项突破性的技术出现之后,何以为继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计算机的硬件也顺利经过了快速的迭代进化,从1946年电子管时代的ENICA,到1954年晶体管时代的TRADIC,再到1964年集成电路时代的IBM 360系列。作为和硬件相伴而生的软件,自然也经过了一段飞跃发展的日子。然而,相比较于硬件毫无悬念的在1971年过渡到微处理器为基础的技术时代,软件却遭遇了一连串的危机。
在电脑的诞生之初,软件通常是单独为了某个特定的计算机而撰写的,例如计算弹道。而随着市场上需求的增加和计算机的普及,在6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可以反复出售的软件产品。据说第一件软件产品诞生在1964年,一家名为ADR的公司开发了一款流程图软件,随后这家公司还为IBM的电脑系统重写了程序。
然而正是因为软件行业的发展,危机也随之出现。当时的软件行业并没有任何通用语言和规范,所有的软件产品都是极度个人化的产物,除了充斥着个人特色的源代码之外,没有任何软件说明文档。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软件危机」的诞生——开发进度和成本失控、维护困难且成本高昂、开发人员和客户无法沟通。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可能影响整个计算机产业的危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在1968年于联邦德国召集了50位计算机编程人员、科学家和工业界巨头,开了一场软件工程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他们不仅第一次确认性的提出了「软件危机」这个词,还同时提出了应对这场危机的词语——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
此后,软件产品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周期模型,有了专业的管理方式和规范。在第二年,UNIX和ARPA网同时诞生,IBM宣布自己的软件产品将和硬件产品分开定价。软件开始从个人化的艺术行为,变成了群体性的商业工程,它终于拥有了独立的生命系统。
在经历了第五次科技革命之后的世界,社会和商业都在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率和表象发展着,越来越快的节奏让人们很难停下来去思考科学本身的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遇见瓶颈?如果有,如何打破?未来科学的走向是哪里?
以及,我们还能不能回到曾经群星璀璨的圆桌旁?抛开已经过于熟悉的产品模式和资本运作,回归科学的本源,去讨论一些纯粹得几乎复古的科学议题。
商业文明的反哺和开创 | GMIC
也许接下来2017年4月27日-5月1日期间,在北京召开的GMIC大会能够满足这种期待。大会将会邀请来自全球的100位顶尖科学家,以「天·工·开·悟」为主题畅谈各自眼中会改变世界的研究成果和方向。往届的GMIC大会曾经汇聚过来自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东京大学以及硅谷等地的各位学术顶尖人物,行业横跨物理学、化学、建筑学、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
而在今年,会议期间G-Summit全球科学创新峰会专场的主题更是定位为「科学复兴」,大有以闭门峰会再现科学家们智慧碰撞时的火花的意味。所谓「科学复兴」,其主旨就是回归推动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科学中寻找人类社会发展难题的破题之道,它和文艺复兴有着相近的意义,即:对于人的解放。
G-Summit是一个拓宽思路、没有疆界的思想碰撞平台。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沟通彼此领域;以科学之名,追问前路,求解未来。
在微信朋友圈里,张亚勤、俞敏洪、沈南鹏、李开复、吴甘沙等二十多位企业家和投资人都加入到了科学的拜物教中,为即将到来的思想盛宴表达兴奋。
美国作家戴维·凯泽写过一本书,题为《嬉皮士救了物理学》,他认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旧金山,是反主流的文化驱动先锋科学家聚在美国的西海岸,抛开学院式的物理教条进行想象和探索,最终为应用科学撞开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理。
或许到了今天,世界仍然需要这样的嬉皮士精神。
声明:本文内容和图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蓝时代网立场。蓝时代 » 互怼、改行、剿灭危机,科学界开起会来总不会无聊
 蓝时代
蓝时代